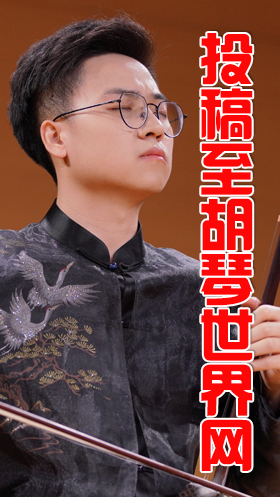介绍:·樊 荣 整理 ·[整理附记] 趁我国著名的二胡演奏家闵惠芬到北京来 举行师生音乐会之机,受领导委派, 由唐锐老师带着我于 2002 年 6 月 26

·樊 荣 整理 ·
[整理附记] 趁我国著名的二胡演奏家闵惠芬到北京来 举行师生音乐会之机,受领导委派, 由唐锐老师带着我于 2002 年 6 月 26 日前去拜望了闵惠芬老师。一方面向她转达 中国音乐学院全体师生对她的敬意;另一方面,想就民族音 乐的发展和学校的音乐教育等问题求教于她。闵惠芬老师 热情地接待 了我们 ,并十分诚恳地 回答 了我们所有 的问题。下面即是这次访谈的记录整理稿。
樊:您对中国民族器乐的现状有什么看法?中国民乐要 更好地发展,应该做哪些方面的努力?
闵:我觉得现在正是民族音乐整个形势在好转的一个 过度时期。我们大家都知道,“文革”十年动乱期间,四人帮 对民族音乐摧残得很厉害、几乎扼杀殆尽。像我们这样的 人,也可以说是一些幸存者。文革中起码有 8 年时间不让我 上台演出,人生有几个 8 年?可是我就是满心的不服气,内 心充满着愤懑。而且一直坚持着练琴、练功,所以当一旦有 了机会的时候,我一下子冒了出来。包括还有像刘德海先 生、胡天泉先生、刘明源先生。那个阶段已经是文革的后期 了,美国费城交响乐团来到中国,要听中国的音乐,当时就 由我们几个人接待了交响乐团的专业音乐家们。我们的演 奏真的是震撼了他们,我拉完《江河水》的时候,那些朋友们 长时间的鼓掌,到后来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等了很久, 才开始拉第二首曲子。经历了这些之后就更加增强了我的 信心。
但是文革结束以后,国家百废待兴,人民生活贫困,国 家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,在这个时候有谁会想中国民 族音乐的事业呢?而且后来又是港台流行音乐的泥沙俱下, 同时经济大潮 的到来 ,使人们在这个时候只想到要去发 财。有一个阶段大家开玩笑地把这种现象叫做“全民经商”,当时又有谁能够去想到民族音乐的发展呢?
也只有到了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,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“弘扬民族文化”这样的口号,而且近几年来又在德育、智 育、体育中加上了美育,强调全民素质教育。 由于有了这样 的政策,专业、业余的民族音乐工作者和音乐院校的专业教 师才能在自己的岗位上辛勤地工作,这样就间接地使民族 音乐的处境有了好转。现在不少地方的民乐考级人数在逐 年增加:5 年前,上海第一次二胡考级只有 400 人参加,今 年则有 6000 多人参加,可见学习民族音乐的阵营在不断地 壮大。对于票房的问题,当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数,但是也 不能简单地以此来说明大家不欢迎民乐。比方说,我们这些 演奏者不仅仅是在大剧场里演出,而且还要经常深入基层, 其时,来看我们上海民族乐团演出的人真是非常的多。同 时,我们还要为中、小学生和大学生演出。无论是从演出效 果来讲,还是从来听音乐会的人数来讲,这几年的进步十分 明显,这终究是对民族音乐的一个促进。我还是对中国的民 族音乐充满着信心,而且我们还意识到:好的形势不是天上 掉下来的。你不能指望,突然某一天,大家都风起云涌地去 看民族器乐音乐会,这总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。我们是靠自 己的辛勤耕耘,到处去播种,默默地培养着我们的后代,这 样才能够使民族音乐的形势有所改变。普及与提高要同时 并举。
樊:您认为要想使中国民族音乐更多地被世界所了解, 我们还应该进行哪些方面的工作?
闵:我国的文化艺术遗产是极其光辉灿烂的。解放以 后,这几十年来又逐渐地形成了一支规模可观的民族音乐 队伍,其中有作曲家、指挥家和演奏家等。这支队伍与解放 前相比,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。像刘天华先生、阿炳,他们 都经常是孤军奋战,而今天我们这支队伍兵强马壮,不仅是 为本国的同胞服务,而且还要跨出国门,打向世界。为了这 样一个目标,我经常是日思夜想。其实像昨天的这样一个演 奏会也呈现了一个侧面:就是用西洋的交响乐队来为中国的民族乐器协奏。试想,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大都有交响乐 队,但中国的民族乐队却不是每个国家都可能有的。因此, 如果说我们有一批非常优秀的民族器乐作品, 由交响乐队 来协奏,那么就可以与当地的交响乐团合作。我也已经有过 这样的合作经历了。我曾经到过俄罗斯,与莫斯科爱乐乐团 合作,他们为我录制了两个多小时的二胡作品。我非常重视 这件事情:预先准备了两个小时以上的乐队总谱,因为没有 谱子就无从演起。我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而做这件事的: 有两个香港人投资 30 万元要为我所演奏过的最优秀的曲 目进行录制,而且要用西洋交响乐团来伴奏。这需要重新配 器,比方说 《长城随想》,它原来由民族乐队伴奏,这次赵建 华演奏的是用西洋交响乐队伴奏的,我请刘文金先生自己 重新配的器。那么就形成了一个曲子有两个版本,这就是我 近几年来所做的最大的一件事:为最优秀的曲 目,配上两种 乐队伴奏形式。这样做的结果,就非常方便走出国门。我还 在德国与他们的交响乐团合作演奏过 《哀歌— 江河水》, 并和德国交响乐团在国内合作过 《良宵》。两次演出都非常 成功,他们交响乐团的总经理给我献花,一束巨大的花。我 当时心里感到好荣耀,民族音乐在国外真是扬眉吐气了。
昨天晚上的演出你们也看到了,是由中央芭蕾舞团交 响乐队伴奏的。他们的演奏十分出色,与独奏者的配合非常 默契,尤其是当演出 《江河水》时,使我浑身激动,寒毛都要 竖起来了,对于这个曲子的演奏,从来没有达到这样高的水 平。其实他们排练的时间只有三天,这样一台演出,有些曲 子还是很有难度的,我认为他们是因为热爱自己的民族音 乐,才会这么认真地表演。尽管由于排练的时间少可能会粗 糙一点,但是我觉得他们的演奏始终充满着激情,这说明学 习西洋音乐的中国人也同样地热爱我们的民族音乐。
樊:比您更老一辈的很多民乐演奏家都是通过 “口传心 授”的方式学习中国民族音乐的;您既通过 “口传心授”的方 式,后来又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,您对中国的民族音乐教育 有什么看法?当前的主要问题是什么?应该以一种什么方式 来教育我们的学生更好?
闵:“口传心授”是其中一个很好的教育形式,但并不是 全部。而我自己的学习主要还是在音乐学院,1958 年我 12 岁进的上音附中,一直是接受正规的学校音乐教育,直到大 学毕业。上海音乐学院— 我的母校— 和我的主课老师 王乙先生、陆修棠先生,以及在学校学习过程中所学习到的 各种音乐理论,都对我终身的演奏事业奠定了非常重要和 坚实的基础。我觉得没有当时的刻苦训练和学习,是不可能 有我今天的成绩的。
我学琴比较早,8 岁就开始随我父亲学习二胡。我父亲 是早期的音乐学院民族音乐专业的学生,他毕业于中央音 乐学院。如果算起来他是刘天华的第三代传人,我是第四代 传人。在我进入上音附中的第一天,金村田校长就给我们提 出了一个口号:“你们学习民族民间音乐,要学深、学透、学到家。”我把这句话当作我终身的座右铭。很小的时候,我就 懂得要收集我们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遗产 。在我 14 岁那 年,第一届 “上海之春”音乐节的时候,听鞠秀芳老师演唱了 一首《阳关三叠》,用古琴伴奏。当时,我一下子就被这个曲 子给迷住了,就到处寻找这个曲谱,可就是找不到,后来我 硬是去把这首作品听会了。以后我学拉《江河水》,也不仅仅 是听二胡的唱片 ,而是 同时 听 民间艺人古新善先生 的演 奏。我们学校的戏曲课、民歌课我都极其认真地去学。直到 现在,大江南北所有省份的民歌我都能背唱一些,这就会对 我终生受益。记得我小时侯认识的一位老先生,他是清代大 侠甘凤慈的后代,他的昆曲唱得很好,我从 10 岁时就和那 位老先生学习昆曲。我所编的二胡曲 《游园惊梦》中的 《游 园》就采用了昆曲音调做基本素材,用几样民族乐器来重 奏,效果很好。像这些作品,今后我都可以带到中国音乐学 院来排练 ,让大家也来与我一起感受传统民族音乐 的味 道。
中国音乐学院的刘德海先生曾说过,十年之内他要准 备请很多位民间音乐艺人来学校教授,这是非常正确的。而 且我还认为:不仅要学生们学,老师更是应该带头学,加油 学。今后不一定都要靠外面的民间艺人来教,我们的老师们 也要会教民间音乐。千万不能只会演奏某一些乐曲,不能只 重视技能训练,而更要重视传统音乐的韵味方面的训练。其 实这是学习民族乐器的一个很重要的侧面。我可以把我终 身积累的东西传授给大家, 同时也很希望去学习同行们所 积累的东西,要不断地扩大自己表演的范围。现在我的表演 曲 目,不光有大家都熟知的作品,同时也有我自己积累的一 些民间音乐,特别是声腔艺术改编为二胡曲的作品。比如像 昨天晚上由我的学生沈晴演奏的 《洪湖主题随想》,这就是 我的第一个自己创作的作品,是根据同名歌剧改编而成的, 它从 1977 年元旦至今,一直久演不衰。再比如,我会寻找一 些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唱段,其中有民歌、古典诗词音乐、曲 艺、戏曲等各种姐妹艺术形式。我要在二胡上试验,将可行 性特别强、好听的音乐改编成二胡新曲,来为观众、听众朋 友服务,往往这种曲子的成功率很高。比方说:一个黄梅戏 小调 《打猪草》,本是活泼、诙谐的对唱,通过二胡来表现就 变成了对奏的形式。这其实非常简单,经常是到某一个地方 演出,当地找一个二胡好手与我同台对奏,就这么一个小作 品观众听得如痴如醉;我还用劳动号子与古曲 《阳关三叠》 改编成了二胡曲,这些是比较浅显的;还有深层次的作品, 譬如用京剧音乐《夜深沉》、南梆子、琵琶古曲《霸王卸甲》这 三个因素组合而成的大型二胡协奏曲,那是技术上高精尖 的作品,非常难演奏。这种与姐妹艺术的结合,把声腔艺术 改编成器乐作品,可以说是我终生的课题。
同时我也一直坚持着学习,无论我走到哪里演出,我都 要学一点东西回去。即使不能编成二胡曲,也可以扩展我的 民间音乐知识面。我去湖南的时候,就总是要请当地花鼓戏 剧团的琴师拉琴给我听,向他请教,看他的指法;我到海南, 去听当地的琼剧;到甘肃、青海,去听花儿,三天三夜和歌手
们围坐在一起,听他们的演唱;到台湾,则去听客家音乐、歌 仔戏、草台戏;甚至平日里我会专程从上海赶到安徽合肥去 看黄梅戏,路上要 6 个小时;有时候在电视中播放戏曲节 目,我会放下手中的一切工作认真地去看 … …。我觉得要不 然自己演奏的作品一定是没有新意的,而由于有了这些补 充,我才会在音乐表现上不断地充实和丰富起来。
樊:我们都知道您是中国最著名的二胡演奏家,您每年 的工作非常忙碌。您的父亲闵季骞教授一生培养教育出许 多的二胡表演人才,您培养出了哪些优秀的二胡表演艺术家?
闵:我很少教学,因为我是上海民族乐团的演员,职业是演奏。我可以说是一个终身的演员,8 岁开始上台演奏,从 来没有停止过演出,除了文革时期和生病期间。我的主要精 力都花在演出以及准备工作上,准备过程往往是最吃力的, 要把一部部作品练出来,同时还要等待首演的机会。因此, 我教的学生不多。这几个学生年龄多在 30 至 40 岁之间,我 称他们是我的老学生。只有沈晴比较小,今年 24 岁,她跟我 学习了三年时间。她是淮剧团的小琴师,就住在我家的楼 下。我发现她是个好苗子,而且有戏曲基础,就很认真地教 她。她也很争气,进步突飞猛进,现在已经考取了新加坡华 乐团。
樊:您曾经多次说过这句话:“生命对于我最大的诱惑 就是事业,离开了心爱的事业,离开了心爱的艺术,生命又有何意义? ”您为什么会对您的二胡事业这么执着?
闵:很多人都知道,我生过一场大病,当然大家都可以 放心,我病后到复出已经有18 年了。有时候,我已经忘记了 自己得过重病, 自认为这是我艺术生涯的第二个春天。现在,我有这么旺盛的经历,工作环境、音乐环境都比过去好了很多,所以我总是带着一种兴高采烈的情绪投入到工作 中去。我每天都忙的一塌糊涂,日程安排也是相当的紧张, 但我觉得这是充实的、令我心满意足。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做 不动了,而只是觉得时间不够用而已。
樊:中国音乐学院的学生们都很喜欢您,您也曾来我们 学校做过讲座。您有什么话要和我们学校的学生们讲?
闵:你们学校的老师都十分优秀,除了你们的爸爸妈妈 望子成龙,你们的老师也同样是望学生成龙的。我听说刘德海老师、曹德维老师都讲过:要请我到你们学校与同学们一 起排练乐曲,把我的一些比较优秀的曲目传授给大家,我等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。
本站资源部分来源于网络,仅供学习交流分享,【胡琴世界网】不承担任何由于内容的使用所引起的争议及损失。如有侵权,可联系管理员删除处理。本文链接:https://www.ihuqin.cn/article/zixun/303.html